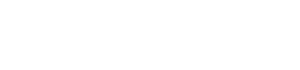个人简介
人物简介
汪胡桢,水利专家。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事水利教育、导淮工程和运河规划等工作,卓有成效。20 世纪50年代初,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主持建设了治理黄河的第一项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促进了我国坝工技术的发展。在从事水利建设的70多年中,他始终坚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教育上学风严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几代水利人才;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进取,主编和编写了多种大型工具书。
汪胡桢,复姓汪胡,名桢,字幹夫,号容盦。浙江省嘉兴市人,1897年7月12日生。15岁时父亲病逝,生活的艰辛使年少的汪胡桢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他刻苦学习,1915年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我国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学生,从此爱上了这个行业,并立志改造自然,征服江河,振兴中华,开始了献身祖国水利事业的光辉的一生。
1922年,汪胡桢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研习水力发电工程。1923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并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曾参加摩尔根瀑布(Morgan Falls)水电站、骚吐斯(Saw-tooth)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使其学业更为坚实。由于当时国内尚无现代水利工程设施,他曾委托美国内务部水利股代为摄制美国水利工程影片一卷,名The Story of Water (《水的事故》,带回国后改译为《水利兴国》),主要内容是讲述水力发电,是不可多得的直观教材,在教学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解欧美水道情况,他到过美国不少地方,参观其闸、坝、堤、渠等。后又去了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使他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开拓了思路。
1924年汪胡桢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1927—1929年,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和浙江水利局副总工程师时,引进了风行欧美的喷射砂浆用的“水泥枪”(Cement Gun),在闻家堰石塘塘面试用,塘缝被封住,塘后覆土不再流失,节省了年修费用。1930年,汪胡桢出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参加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因经费匮缺,计划被束之高阁,但他用英国退赔的庚子赔款,设计建成了计划中的邵伯、淮阴、刘老涧三个船闸。1931年,长江、淮河发大水,堤防、涵闸大都被毁,遍地灾民。他领导修复了西起正阳关、东抵五河县长达200公里的淮河大堤及涵闸几十处,疏浚了淮河支流北淝河。1934年,汪胡桢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亲自踏勘了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仅用一年半的时间,编制完成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一书。因国家多事,此计划未能付诸实现。1946年,汪胡桢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领导修复了因抗日战争破坏的钱塘江海塘缺口。
193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他是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二至第十届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并兼出版委员会主任,主编《水利》月刊,累计出刊13卷75期,对普及和推广水利科学知识,促进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把水利古籍印为《中国水利珍本丛书》,重刊《河渠纪闻》、《治河方略》、《问水集》等珍贵史料。同时,与商务印书馆商妥将汇集四千年治水经验的《行水金鉴》及《续行水金鉴》刊入《万有文库》。1938— 1945年日寇侵华期间,他身处敌伪统治下的上海,坚决不为日寇工作,在上海组织一大批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从事翻译和著作工作。他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工程师旭克列许著的《水利工程学》,该书对各种水工建筑物讲述十分清楚,插图又多,成为当时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工程师手册》,这本书收集了国内外许多宝贵资料,共有基本(理论)、土木、水利三册,这使中国工程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手册,对以后的工程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为了这部巨著,汪胡桢卖掉了房子以支付稿费和出版费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胡桢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后兼治淮委员会委员、工程部部长、佛子岭水库总指挥。1954—1960年,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60—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名誉院长。1978年任水利部顾问。1978—1980年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二届临时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1—1985年分别被选为中国水利学会第三、第四届名誉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第五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顾问。汪胡桢是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委员。
汪胡桢从事水利工作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他虽尽心竭力做了不少水利计划,但由于政府腐败而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汪胡桢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为此,他满怀热情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水利事业中,为我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修建中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
20世纪50年代初,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刚问世不久,仅美国及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土地上,却矗立起一座由中国工程师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这不仅在当时被国内水工界视为奇迹,就连外国专家也跷起了大拇指说:“连拱坝好,中国工程师了不起。”这座水库的设计和施工,就是汪胡桢主持的。
1950年,汪胡桢担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制定“治淮方略”,他和钱正英在曾山同志的领导下,专程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积极支持。“治淮方略”一获批准,汪胡桢就率领工程大军前往大别山区,筹建“治淮方略” 中主要工程措施之一的佛子岭水库。
佛子岭水库选用什么坝型是至关重要的首要问题。当时提出了混凝土重力坝、土坝、钢筋混凝土平板坝及连拱坝四种方案。汪胡桢竭力推荐采用连拱坝,它的体积仅为重力坝的1/5。该水库规模宏大,技术复杂,加之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正在进行,经济技术落后,资金不足,水泥、钢材奇缺,施工机械更缺,连振捣器都没有,且大别山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因此,必须节省水泥。由于连拱坝在国内首次采用,加之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器材、资料无法取得,连拱坝的设计施工及抗震性能的计算比重力坝复杂得多,因此一开始不易被人们接受,甚至苏联专家也认为无法实现。有好心人劝他不必坚持。汪胡桢经过认真分析,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连拱坝结构单薄,能否抗御横向地震是争论的主要问题。汪胡桢通过对连拱坝的稳定问题进行详细分析计算,认为坝基摩擦力能抵抗水库盈满时的水推力,横向地震时每一个垛墙都能抵抗地震力而有余,并组织技术人员分析计算,证明了应力能为结构强度所抵抗住。每个垛都能稳定,由拱连接起来则相互依存,稳定将更有保证。就这样,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和争论,终于获得专家们和领导的赞同,决定采用连拱坝。
建水库,先修路。佛子岭水库位于淮河上游淠河上,交通不便,在山区残匪尚未剿清的情况下,汪胡桢冒险探路,连日颠簸奔跑,反复视察每个弯道和应建桥梁之处。公路建成后,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云集佛子岭,各种建设物资、器材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工地。
佛子岭水库坝高74米,长500余米,混凝土总体积不到20 万立方米(如果采用重力坝坝型,浇筑混凝土就需要100万立方米)。这是一种轻型支墩坝,体积小,但结构复杂,这样大型的工程施工,在过去我国没有人搞过。汪胡桢精心策划,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坝体施工中,缺乏升高塔和拱模板,如果采用常规的木模,只一次性使用,浪费太大,速度慢,且随坝体升高拱模板制作困难。汪胡桢亲自领导设计了用砂箱为支座的半圆拱滑升钢模壳,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吊升和拆模甚为灵活。这个方法不仅节省了大量钢材,而且加快了施工进度,特别丰富了设计人员的思路。接着他又为拱圈浇筑混凝土拟出流水作业程序,大大节时省力。为确保薄结构连拱坝坚固耐久,汪胡桢查阅国内外资料,筹建混凝土实验室,派人外出学习。他将习惯常用的水泥配料体积比改为重量比,定出了各部位混凝土的级配,使用天然河卵石代替人工碎石作骨料,并在混凝土中外加添加剂,提高了混凝土的可塑性、密实性和耐久性。这些措施当时在国内都属于首创,为创建高质量的混凝土连拱坝奠定了科学基础。
经过三年苦战,1954年冬,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亚洲第一座连拱坝,终于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如今连拱坝已平安度过50个春秋,历经洪水考验,至今坝面碳化度轻微。佛子岭水库的建成,开创了连拱坝在我国水工建筑史上的新纪元,推动了我国坝工技术的发展,汪胡桢也由此获得“中国连拱坝之父”的美称。随后,我国又在梅山水库建成了当时世界最高的连拱坝,从而提高了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
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
汪胡桢一生坚持科学立场,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早在1936年,汪胡桢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倡导并亲自起草了《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信条七则》。这七条是:
(一)应绝对相互尊重职业的名誉与地位;
(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之下,应极端尊重技术上应有之人格与操守;
(三)不得违反科学的论据,提出或施行任何工程计划;
(四)搜集及分析技术上之资料时,应绝对地忠实;
(五)对于任何水利工程主张,有相反之论断时,应作善意之商权,不得作恶意之攻击;
(六)任何人员对于水利有错误的主张时,不得率意附同;
(七)对会员或其他水利工程师的工作,应尽量协助,不得牵制或排挤。
汪胡桢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就是这样遵循以上原则,身体力行。佛子岭水库施工中,汪胡桢对工程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一次混凝土施工,曾在垛墙的外墙边缘嵌了一条约5厘米宽的麻袋片,为此事,整个工地停工整顿一天,并把这一天定为“工程质量日”。在基坑开挖中,汪胡桢严格要求,在基坑岩石上浇混凝土前,必须用水清洗基坑,并用抹布擦干水迹,方可浇筑。这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在后来的各项工程建设中,一直采用汪胡桢交代的这个老传统。
1956年初,汪胡桢和李鹗鼎同时被任命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总工程师。三门峡水库工程是黄河治理规划中的第一项工程,汪胡桢虽年近花甲,但朝夕都在施工前线指挥。他工作认真负责,决不搞“想当然”,而要弄清楚“所以然”,从“所以然”中开拓新思路,发现新问题。三门峡大坝是重力坝,对大体积的分仓浇筑、分区标号设计和温度控制、并缝灌浆等问题,汪胡桢都进行认真的研究。浇筑大坝混凝土时,提出按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标号的水泥,从而节约了大量的水泥。研究提出并缝要求多少水泥浆进入缝隙后才能传递应力。大坝混凝土浇筑冷却是个技术难题,他提出在坝体预埋冷却水管,水泥中加冰水冷却的措施,成功地保证了大坝的浇筑质量。此外,他还提出大面积通仓浇筑的设想,当时虽然限于条件未能实现,但是到了20世纪90 年代,则被较为普遍地付诸实施了。
三门峡水库是委托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设计的。对设计院送来的设计文件和图纸,他都逐一审阅,有时还进行复算。在“大跃进”年代里,他不赞成学习苏联经验搞形而上学,而是从实际出发。对苏联专家的建议也要认真思考分析,一分为二。在施工中发生与苏联专家原设计意见不一致时,他总是实事求是,决不盲从。如梳齿工程开挖,苏联专家提出2/3的设计开挖线,也就是要保留1/3高度作为防震保护层。但这样进度慢,不能保证施工在一个枯水季节完成。汪胡桢与苏联专家商量,通过试验,提出深孔爆破,一次即可达到设计开挖线1.5米的保护层,并不影响下面的岩层。采用这一办法施工后,开挖进度大大加快,提前完成了任务。在截流设计上,原设计是在神门浅水道预建一道截流闸。1957年春,大水把已建好的一个闸墩冲走,苏联专家仍坚持恢复闸墩,汪胡桢则提出打拦石桩代替原修闸方案。该方案被采用后,既节省了时间和费用,也保证了截流的成功。最后,苏联专家十分佩服汪胡桢尊重科学、敢于实践的精神。
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三门峡时,有一位水文工程师未能回答上周总理提的关于泥沙对三门峡水库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汪胡桢便上前解围,将泥沙情况简明扼要地讲清楚。周总理很满意,十分尴尬的场面又活跃起来。三门峡的泥沙问题,汪胡桢认为,植树造林、修梯田等措施是有效的,但50年后入库沙量仍可减少50%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对泥沙问题要实事求是,科学论证,不能搞主观主义。汪胡桢指出三门峡工程的排沙孔太小,会给将来的水库运行带来问题,因而他主张排沙孔的设计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他建议多设排沙底孔,并降低孔口高程。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意见未被采用。后来三门峡水库蓄水不久,泥沙淤积严重,不得不采取泄水排沙的紧急措施和长达13年之久的改造。事实证明汪胡桢的见解是正确的。
事后有人把三门峡出现的泥沙问题归结为苏联专家的设计,汪胡桢却宽容地说: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是以我国提供的资料作为设计依据的,该院的专家毕竟是外国人,对三门峡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我们应保持头脑冷静,遵循科学的原则,实事求是,不能跟风跑、随风倒,要有自己的主见。
对于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汪胡桢认为必须有助于我国水利技术科学的进步。1957年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大会上,汪胡桢发言,对此提出了5点建议:第一,国内能够设计的不应委托国外。第二,如属可能,应邀请专家来华设计。这样可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加以消化,用来提高我国在水利工程上的技术科学水平。第三,委托国外设计须先摸清外国技术的底。第四,委托国外设计须做好规划。三门峡就是前车之鉴。第五,在国外设计时国内须进行平行设计。因为一个工程在设计时候,一定会遇到许多科学上没有解决的新问题。自己不做,别人为你劳动,结果自己一无所得。汪胡桢说,技术科学的研究是一点也假借不得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侥幸取巧、贪图便宜是不可能的。
造就了几代水利建设人才
汪胡桢本人不仅在水利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早在1924年,汪胡桢留学归来返回母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他热心于有关教学的各项事宜。为保存水利典籍,他积极收集、出版了《水利丛钞》,组织建筑工程实验室,积极参与筹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舍,四处奔波,自筹资金。汪胡桢认为学校只采用外国教科书非长久之计,他在授课之余,专心从事著作,编成《给水工程学》、《水力学》等书。此外,他还将自己珍藏的水利古籍捐赠给学校图书馆,其中有《金陵后湖志》、《丁草刘白疆域》、《属东驳议》、《御制数理精蕴》等,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湖北籍学友会还得到了他捐赠的《Hydraulic Turbine Installations》(《水轮机设备》)。1933年,在他的建议下,创办了一所学费很低的公益性学校——高级土木科,学制一年,既为众多有志求学而无力上大学及求职无门的青年解决了难题,又培养了一批中级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土木科办了两届,共64人,毕业后的学生,多数人由汪胡桢协同校方介绍到导淮委员会、江苏省公路管理处等工程技术单位,获得社会的好评。大多数毕业生至今一直坚持在水利、土木、建筑等岗位上,有的经过更进一步深造,现已成为大学教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35年,在汪胡桢建议下,利用工赈余款,以他为主考,录取了严恺、张书农、王鹤亭、伍诚、粟宗嵩、徐怀云、薛履坦等分赴英、美、德、法、荷、印度留学,后来他们都成为我国卓越的水利专家。
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时,人才奇缺,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边干边学。汪胡桢把从国外带回的书送到图书馆,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书;他亲自讲授“坝工设计守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施工结构及内拱钢模的设计与使用”等课程。他为人谦虚和蔼,诲人不倦,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这所工地大学培养了一代新人,如曹楚生、曹宏勋、朱起凤等,现已成为技术骨干和有名的水利专家,在水利建设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汪胡桢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理论联系实际是他一贯的教学之道,他除编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和学生的生产实践。1965年,已67岁的汪胡桢,还亲自带领师生,去黄河中游碛口实地勘测设计,住窑洞、吃粗粮,完成了《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后因“文化大革命”,此方案未能实施,但他为治黄事业倾注自己心血的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治学风范,一直为人们所称道。汪胡桢见学院图书馆图书不多,又曾两次慷慨捐藏书2000余册。第一次是他从浙江老家将80年来积累的1500余册藏书自费运到北京,赠送给学院图书馆;第二次是在临终前的几天里,自己整理好几只大纸箱,除了留下一部分工具书外,全部送给了学院。汪胡桢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但当人们要宣传他时,他却说:“我已经老了,应该多留些版面给那些有贡献的中青年同志。”
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进取
20世纪7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刚开始引进我国,全国尚未普及的时候,汪胡桢就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水利工程中。地下洞室的力学分析是最繁琐的工作,不仅费时,且易出错,是设计人员最感头痛的事。为此,汪胡桢撰写了《地下洞室的结构设计》一书。该书以地下洞室中最常用的圈门式结构为准,推导出力学分析中全部所需公式、载常数的一般算式,并用电子计算机算出上述常数值,列成计算表以供查用。如此就能大大加快计算速度,提高设计质量。随着现代工程及管理数学的蓬勃兴起和计算机计算技术的发展,汪胡桢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数学对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及作用。于是,汪胡桢积极发起、组织了工程及管理方面的数学家,主编了500余万字的大型工具书——《现代工程数学手册》,其中基础部分是他亲自撰写的。该书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数学工具书,在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学工作者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汪胡桢编著这本书时,已年逾八旬,身患糖尿病、腿部神经炎、白内障,走路艰难,左眼失明,右眼只有0.1视力,看书写字需用高倍放大镜,每天伏案工作六七个小时,甚至大年初一也不休息。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世界瞩目的巨大工程,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是汪胡桢早就有的愿望。1958年春,汪胡桢随同周恩来总理查勘长江三峡,他纵览江水滔滔不舍昼夜地向东流去,把宝贵的能源完全消耗掉,不禁感慨万分,当即写下一首《展望长江三峡》诗:“三峡滔滔年又年,资源耗尽少人怜。猿声早逐轻舟去,客梦徒为急濑牵。会置轮机舒水力,更横高坝镇深渊。他时紫电传千里,神女应惊人胜天。”当时周总理看了笑道:“你双姓汪胡,又有工程师与诗人的双重人格。长江三峡的巨大能源是要开发的。”1983年,汪胡桢参加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探讨,他激动不已,发出“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还想背上行李去三峡工地大干一场”的坚强心声。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力不从心,于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三峡工程出谋划策上面,先后发表了20多篇有关三峡大坝选型、船闸设计与移民工作等重大科研课题的论文,提出了不少大胆独创的设计构想。例如三峡坝型这一课题,他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设计、计算,提出了“格箱式浇筑法代替柱状法”,设想创造混凝土格箱和土石格箱坝两种坝型。船闸是三峡工程中难度较大的一项工程,汪胡桢研究了古今中外的船闸,大胆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使江船一步升降137米水位差的井式船闸方案。我国自己能不能不靠外援而自行设计呢? 他老人家充满信心地说:“其实任何人设计水工建筑物都是从零开始的。我国几十年来的水利建设工程,除三门峡水库外,都是自己设计的。”他谆谆告诫大家:“不要忘记世界上首先发明船闸的是我国的先哲,这项发明领先于欧美各国两个世纪。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希望我国水利科学工作者能深入研究。
水库淹没区的居民迁移问题是建库工程中耗资巨大,且工作十分棘手的问题。过去是实行国家发给移民迁移费自行解决,此办法遗留问题多。后来用移民费建设移民区,虽然克服了不少移民生活居住困难的问题,但生产资料、发展生产等问题还没有解决。汪胡桢写出《怎样实施长江三峡水库经济开发性移民政策》的论文,他提出,应给移民营建经济林、建设水库渔业基地及兴办新工业区,使移民不但能在新地区居住生活,而且能从事生产,使移民费用变成企业投资,而后以生产税利形式再缴给国家。他的这种开发性的思想,在还没有市场经济观念的1983 年提出,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得到了水利部领导的重视。如今,开发性移民政策已成为主要的移民政策。
汪胡桢很注重水利建设的经济效益。1981年,他写出了《水电工程的经济核算》、《自力更生开发水利资源》、《开发长江三峡水利必须改革经营体制》等论文,很早就意识到经济与市场的观念。他还建议长江水利从建设三峡水库起,就应采用企业体制作为经营方针,并对成立长江水利开发公司的组织、任务、效益作了具体的规划和分析。晚年的汪胡桢,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在水利科技上孜孜追求,锲而不舍;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不断探索进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汪胡桢一生著作甚多,根据国内有关图书馆编印的目录和汪胡桢亲属提供的资料统计,汪胡桢的著作(含编、译)达10本之多,公开发表的论文有41篇,未公开发表的有48篇,其他如回忆录、报告、发言等文章有45 篇。他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为水利事业已经作出那么多贡献的汪胡桢,仍自感不足。1989年9月,他得知有医术高明的苏联眼科专家来华的消息后,下决心要去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以求恢复视力重新笔耕。不料,20多天后的1989年10月13日,他竟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光辉的榜样》一文中写道:“他毋需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贾本琪)
简 历
1897年7月12日 生于浙江省嘉兴市。
1917年 毕业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1922—1923年 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1923—1924年 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
1924—1926年 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
1927年 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
1929年 任浙江省水利局副总工程师。
1930—1931年 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第十二区工赈局局长兼皖淮主任工程师。
1931—1949年 1931年起历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二至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兼出版委员会主任。1936年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
1934年 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
1935—1937年 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设计科长。
1938—1945年 先后在中国科学社、厚生出版社译书、编书。
1946年 任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赈务组副组长,水利委员会派驻联合国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顾问。
1946—1948年 任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9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1950—1954年 任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兼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工程部部长,佛子岭工程总指挥。
1954—1960年 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
1955年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60—1978年 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名誉院长。
1978—1982年 任水利部顾问。
1989年10月13日 逝世于北京。
主 要 论 著
1 汪胡桢,周文德,李藕庄,等. 中国工程师手册.上海:厚生出版社,1944.
2 汪胡桢. 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7.
3 汪胡桢. 地下洞室的结构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
4 汪胡桢. 罗汝梅,杨真荣,等.现代工程数学手册.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
5 汪胡桢. 重力坝的主应力网.北京:水利学报,1981(6):61-666.
6 汪胡桢. 长江三峡节水船闸的初步探讨.北京:水利学报,1983(7):47-537.
7 汪胡桢. 怎样实施长江三峡水库经济开发性移民政策.武汉:人民长江,1987(5):2-4.
参 考 文 献
[1]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代水工汪胡桢.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2]钱正英.光辉的榜样——向汪胡桢先生学习.中国水利,1989(12):3.
[3]李鹗鼎.怀念汪总.中国水利,1989(12):6.
人物简介
汪胡桢,水利专家。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事水利教育、导淮工程和运河规划等工作,卓有成效。20 世纪50年代初,他主持修建了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主持建设了治理黄河的第一项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促进了我国坝工技术的发展。在从事水利建设的70多年中,他始终坚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在教育上学风严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了几代水利人才;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进取,主编和编写了多种大型工具书。
汪胡桢,复姓汪胡,名桢,字幹夫,号容盦。浙江省嘉兴市人,1897年7月12日生。15岁时父亲病逝,生活的艰辛使年少的汪胡桢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他刻苦学习,1915年中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我国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学生,从此爱上了这个行业,并立志改造自然,征服江河,振兴中华,开始了献身祖国水利事业的光辉的一生。
1922年,汪胡桢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研习水力发电工程。1923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并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曾参加摩尔根瀑布(Morgan Falls)水电站、骚吐斯(Saw-tooth)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使其学业更为坚实。由于当时国内尚无现代水利工程设施,他曾委托美国内务部水利股代为摄制美国水利工程影片一卷,名The Story of Water (《水的事故》,带回国后改译为《水利兴国》),主要内容是讲述水力发电,是不可多得的直观教材,在教学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解欧美水道情况,他到过美国不少地方,参观其闸、坝、堤、渠等。后又去了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家,使他增长了见识,打开了眼界,开拓了思路。
1924年汪胡桢回国后,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1927—1929年,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和浙江水利局副总工程师时,引进了风行欧美的喷射砂浆用的“水泥枪”(Cement Gun),在闻家堰石塘塘面试用,塘缝被封住,塘后覆土不再流失,节省了年修费用。1930年,汪胡桢出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参加制定了导淮工程计划,因经费匮缺,计划被束之高阁,但他用英国退赔的庚子赔款,设计建成了计划中的邵伯、淮阴、刘老涧三个船闸。1931年,长江、淮河发大水,堤防、涵闸大都被毁,遍地灾民。他领导修复了西起正阳关、东抵五河县长达200公里的淮河大堤及涵闸几十处,疏浚了淮河支流北淝河。1934年,汪胡桢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亲自踏勘了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仅用一年半的时间,编制完成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一书。因国家多事,此计划未能付诸实现。1946年,汪胡桢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领导修复了因抗日战争破坏的钱塘江海塘缺口。
1931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成立,他是创始人之一,历任第二至第十届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并兼出版委员会主任,主编《水利》月刊,累计出刊13卷75期,对普及和推广水利科学知识,促进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把水利古籍印为《中国水利珍本丛书》,重刊《河渠纪闻》、《治河方略》、《问水集》等珍贵史料。同时,与商务印书馆商妥将汇集四千年治水经验的《行水金鉴》及《续行水金鉴》刊入《万有文库》。1938— 1945年日寇侵华期间,他身处敌伪统治下的上海,坚决不为日寇工作,在上海组织一大批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从事翻译和著作工作。他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工程师旭克列许著的《水利工程学》,该书对各种水工建筑物讲述十分清楚,插图又多,成为当时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工程师手册》,这本书收集了国内外许多宝贵资料,共有基本(理论)、土木、水利三册,这使中国工程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手册,对以后的工程技术人员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为了这部巨著,汪胡桢卖掉了房子以支付稿费和出版费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胡桢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后兼治淮委员会委员、工程部部长、佛子岭水库总指挥。1954—1960年,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局总工程师。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60—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名誉院长。1978年任水利部顾问。1978—1980年任中国水利学会第二届临时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1—1985年分别被选为中国水利学会第三、第四届名誉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第五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顾问。汪胡桢是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六届委员。
汪胡桢从事水利工作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他虽尽心竭力做了不少水利计划,但由于政府腐败而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汪胡桢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为此,他满怀热情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祖国的水利事业中,为我国水利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修建中国第一座混凝土连拱坝
20世纪50年代初,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刚问世不久,仅美国及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土地上,却矗立起一座由中国工程师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佛子岭水库大坝。这不仅在当时被国内水工界视为奇迹,就连外国专家也跷起了大拇指说:“连拱坝好,中国工程师了不起。”这座水库的设计和施工,就是汪胡桢主持的。
1950年,汪胡桢担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与制定“治淮方略”,他和钱正英在曾山同志的领导下,专程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得到总理的积极支持。“治淮方略”一获批准,汪胡桢就率领工程大军前往大别山区,筹建“治淮方略” 中主要工程措施之一的佛子岭水库。
佛子岭水库选用什么坝型是至关重要的首要问题。当时提出了混凝土重力坝、土坝、钢筋混凝土平板坝及连拱坝四种方案。汪胡桢竭力推荐采用连拱坝,它的体积仅为重力坝的1/5。该水库规模宏大,技术复杂,加之新中国成立不久,抗美援朝正在进行,经济技术落后,资金不足,水泥、钢材奇缺,施工机械更缺,连振捣器都没有,且大别山区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因此,必须节省水泥。由于连拱坝在国内首次采用,加之美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器材、资料无法取得,连拱坝的设计施工及抗震性能的计算比重力坝复杂得多,因此一开始不易被人们接受,甚至苏联专家也认为无法实现。有好心人劝他不必坚持。汪胡桢经过认真分析,坚信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连拱坝结构单薄,能否抗御横向地震是争论的主要问题。汪胡桢通过对连拱坝的稳定问题进行详细分析计算,认为坝基摩擦力能抵抗水库盈满时的水推力,横向地震时每一个垛墙都能抵抗地震力而有余,并组织技术人员分析计算,证明了应力能为结构强度所抵抗住。每个垛都能稳定,由拱连接起来则相互依存,稳定将更有保证。就这样,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和争论,终于获得专家们和领导的赞同,决定采用连拱坝。
建水库,先修路。佛子岭水库位于淮河上游淠河上,交通不便,在山区残匪尚未剿清的情况下,汪胡桢冒险探路,连日颠簸奔跑,反复视察每个弯道和应建桥梁之处。公路建成后,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云集佛子岭,各种建设物资、器材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工地。
佛子岭水库坝高74米,长500余米,混凝土总体积不到20 万立方米(如果采用重力坝坝型,浇筑混凝土就需要100万立方米)。这是一种轻型支墩坝,体积小,但结构复杂,这样大型的工程施工,在过去我国没有人搞过。汪胡桢精心策划,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坝体施工中,缺乏升高塔和拱模板,如果采用常规的木模,只一次性使用,浪费太大,速度慢,且随坝体升高拱模板制作困难。汪胡桢亲自领导设计了用砂箱为支座的半圆拱滑升钢模壳,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吊升和拆模甚为灵活。这个方法不仅节省了大量钢材,而且加快了施工进度,特别丰富了设计人员的思路。接着他又为拱圈浇筑混凝土拟出流水作业程序,大大节时省力。为确保薄结构连拱坝坚固耐久,汪胡桢查阅国内外资料,筹建混凝土实验室,派人外出学习。他将习惯常用的水泥配料体积比改为重量比,定出了各部位混凝土的级配,使用天然河卵石代替人工碎石作骨料,并在混凝土中外加添加剂,提高了混凝土的可塑性、密实性和耐久性。这些措施当时在国内都属于首创,为创建高质量的混凝土连拱坝奠定了科学基础。
经过三年苦战,1954年冬,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也是亚洲第一座连拱坝,终于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如今连拱坝已平安度过50个春秋,历经洪水考验,至今坝面碳化度轻微。佛子岭水库的建成,开创了连拱坝在我国水工建筑史上的新纪元,推动了我国坝工技术的发展,汪胡桢也由此获得“中国连拱坝之父”的美称。随后,我国又在梅山水库建成了当时世界最高的连拱坝,从而提高了我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
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
汪胡桢一生坚持科学立场,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早在1936年,汪胡桢在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六届年会上倡导并亲自起草了《中国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职业道德信条七则》。这七条是:
(一)应绝对相互尊重职业的名誉与地位;
(二)无论处于何种环境之下,应极端尊重技术上应有之人格与操守;
(三)不得违反科学的论据,提出或施行任何工程计划;
(四)搜集及分析技术上之资料时,应绝对地忠实;
(五)对于任何水利工程主张,有相反之论断时,应作善意之商权,不得作恶意之攻击;
(六)任何人员对于水利有错误的主张时,不得率意附同;
(七)对会员或其他水利工程师的工作,应尽量协助,不得牵制或排挤。
汪胡桢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就是这样遵循以上原则,身体力行。佛子岭水库施工中,汪胡桢对工程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一次混凝土施工,曾在垛墙的外墙边缘嵌了一条约5厘米宽的麻袋片,为此事,整个工地停工整顿一天,并把这一天定为“工程质量日”。在基坑开挖中,汪胡桢严格要求,在基坑岩石上浇混凝土前,必须用水清洗基坑,并用抹布擦干水迹,方可浇筑。这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施工队伍。在后来的各项工程建设中,一直采用汪胡桢交代的这个老传统。
1956年初,汪胡桢和李鹗鼎同时被任命为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总工程师。三门峡水库工程是黄河治理规划中的第一项工程,汪胡桢虽年近花甲,但朝夕都在施工前线指挥。他工作认真负责,决不搞“想当然”,而要弄清楚“所以然”,从“所以然”中开拓新思路,发现新问题。三门峡大坝是重力坝,对大体积的分仓浇筑、分区标号设计和温度控制、并缝灌浆等问题,汪胡桢都进行认真的研究。浇筑大坝混凝土时,提出按不同部位采用不同标号的水泥,从而节约了大量的水泥。研究提出并缝要求多少水泥浆进入缝隙后才能传递应力。大坝混凝土浇筑冷却是个技术难题,他提出在坝体预埋冷却水管,水泥中加冰水冷却的措施,成功地保证了大坝的浇筑质量。此外,他还提出大面积通仓浇筑的设想,当时虽然限于条件未能实现,但是到了20世纪90 年代,则被较为普遍地付诸实施了。
三门峡水库是委托前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设计的。对设计院送来的设计文件和图纸,他都逐一审阅,有时还进行复算。在“大跃进”年代里,他不赞成学习苏联经验搞形而上学,而是从实际出发。对苏联专家的建议也要认真思考分析,一分为二。在施工中发生与苏联专家原设计意见不一致时,他总是实事求是,决不盲从。如梳齿工程开挖,苏联专家提出2/3的设计开挖线,也就是要保留1/3高度作为防震保护层。但这样进度慢,不能保证施工在一个枯水季节完成。汪胡桢与苏联专家商量,通过试验,提出深孔爆破,一次即可达到设计开挖线1.5米的保护层,并不影响下面的岩层。采用这一办法施工后,开挖进度大大加快,提前完成了任务。在截流设计上,原设计是在神门浅水道预建一道截流闸。1957年春,大水把已建好的一个闸墩冲走,苏联专家仍坚持恢复闸墩,汪胡桢则提出打拦石桩代替原修闸方案。该方案被采用后,既节省了时间和费用,也保证了截流的成功。最后,苏联专家十分佩服汪胡桢尊重科学、敢于实践的精神。
1958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三门峡时,有一位水文工程师未能回答上周总理提的关于泥沙对三门峡水库有什么影响的问题,汪胡桢便上前解围,将泥沙情况简明扼要地讲清楚。周总理很满意,十分尴尬的场面又活跃起来。三门峡的泥沙问题,汪胡桢认为,植树造林、修梯田等措施是有效的,但50年后入库沙量仍可减少50%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对泥沙问题要实事求是,科学论证,不能搞主观主义。汪胡桢指出三门峡工程的排沙孔太小,会给将来的水库运行带来问题,因而他主张排沙孔的设计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他建议多设排沙底孔,并降低孔口高程。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意见未被采用。后来三门峡水库蓄水不久,泥沙淤积严重,不得不采取泄水排沙的紧急措施和长达13年之久的改造。事实证明汪胡桢的见解是正确的。
事后有人把三门峡出现的泥沙问题归结为苏联专家的设计,汪胡桢却宽容地说: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是以我国提供的资料作为设计依据的,该院的专家毕竟是外国人,对三门峡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多,我们应保持头脑冷静,遵循科学的原则,实事求是,不能跟风跑、随风倒,要有自己的主见。
对于委托国外设计水利工程,汪胡桢认为必须有助于我国水利技术科学的进步。1957年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大会上,汪胡桢发言,对此提出了5点建议:第一,国内能够设计的不应委托国外。第二,如属可能,应邀请专家来华设计。这样可以吸收外国的长处加以消化,用来提高我国在水利工程上的技术科学水平。第三,委托国外设计须先摸清外国技术的底。第四,委托国外设计须做好规划。三门峡就是前车之鉴。第五,在国外设计时国内须进行平行设计。因为一个工程在设计时候,一定会遇到许多科学上没有解决的新问题。自己不做,别人为你劳动,结果自己一无所得。汪胡桢说,技术科学的研究是一点也假借不得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侥幸取巧、贪图便宜是不可能的。
造就了几代水利建设人才
汪胡桢本人不仅在水利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早在1924年,汪胡桢留学归来返回母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他热心于有关教学的各项事宜。为保存水利典籍,他积极收集、出版了《水利丛钞》,组织建筑工程实验室,积极参与筹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校舍,四处奔波,自筹资金。汪胡桢认为学校只采用外国教科书非长久之计,他在授课之余,专心从事著作,编成《给水工程学》、《水力学》等书。此外,他还将自己珍藏的水利古籍捐赠给学校图书馆,其中有《金陵后湖志》、《丁草刘白疆域》、《属东驳议》、《御制数理精蕴》等,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湖北籍学友会还得到了他捐赠的《Hydraulic Turbine Installations》(《水轮机设备》)。1933年,在他的建议下,创办了一所学费很低的公益性学校——高级土木科,学制一年,既为众多有志求学而无力上大学及求职无门的青年解决了难题,又培养了一批中级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高级土木科办了两届,共64人,毕业后的学生,多数人由汪胡桢协同校方介绍到导淮委员会、江苏省公路管理处等工程技术单位,获得社会的好评。大多数毕业生至今一直坚持在水利、土木、建筑等岗位上,有的经过更进一步深造,现已成为大学教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1935年,在汪胡桢建议下,利用工赈余款,以他为主考,录取了严恺、张书农、王鹤亭、伍诚、粟宗嵩、徐怀云、薛履坦等分赴英、美、德、法、荷、印度留学,后来他们都成为我国卓越的水利专家。
在修建佛子岭水库时,人才奇缺,他带领一批知识分子边干边学。汪胡桢把从国外带回的书送到图书馆,成为大家争相借阅的书;他亲自讲授“坝工设计守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施工结构及内拱钢模的设计与使用”等课程。他为人谦虚和蔼,诲人不倦,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这所工地大学培养了一代新人,如曹楚生、曹宏勋、朱起凤等,现已成为技术骨干和有名的水利专家,在水利建设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0年,汪胡桢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理论联系实际是他一贯的教学之道,他除编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和学生的生产实践。1965年,已67岁的汪胡桢,还亲自带领师生,去黄河中游碛口实地勘测设计,住窑洞、吃粗粮,完成了《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后因“文化大革命”,此方案未能实施,但他为治黄事业倾注自己心血的精神和身体力行的治学风范,一直为人们所称道。汪胡桢见学院图书馆图书不多,又曾两次慷慨捐藏书2000余册。第一次是他从浙江老家将80年来积累的1500余册藏书自费运到北京,赠送给学院图书馆;第二次是在临终前的几天里,自己整理好几只大纸箱,除了留下一部分工具书外,全部送给了学院。汪胡桢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水利建设人才。但当人们要宣传他时,他却说:“我已经老了,应该多留些版面给那些有贡献的中青年同志。”
在学术上不断探索进取
20世纪70年代末,计算机技术刚开始引进我国,全国尚未普及的时候,汪胡桢就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水利工程中。地下洞室的力学分析是最繁琐的工作,不仅费时,且易出错,是设计人员最感头痛的事。为此,汪胡桢撰写了《地下洞室的结构设计》一书。该书以地下洞室中最常用的圈门式结构为准,推导出力学分析中全部所需公式、载常数的一般算式,并用电子计算机算出上述常数值,列成计算表以供查用。如此就能大大加快计算速度,提高设计质量。随着现代工程及管理数学的蓬勃兴起和计算机计算技术的发展,汪胡桢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数学对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及作用。于是,汪胡桢积极发起、组织了工程及管理方面的数学家,主编了500余万字的大型工具书——《现代工程数学手册》,其中基础部分是他亲自撰写的。该书是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数学工具书,在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学工作者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汪胡桢编著这本书时,已年逾八旬,身患糖尿病、腿部神经炎、白内障,走路艰难,左眼失明,右眼只有0.1视力,看书写字需用高倍放大镜,每天伏案工作六七个小时,甚至大年初一也不休息。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世界瞩目的巨大工程,开发长江三峡水力资源是汪胡桢早就有的愿望。1958年春,汪胡桢随同周恩来总理查勘长江三峡,他纵览江水滔滔不舍昼夜地向东流去,把宝贵的能源完全消耗掉,不禁感慨万分,当即写下一首《展望长江三峡》诗:“三峡滔滔年又年,资源耗尽少人怜。猿声早逐轻舟去,客梦徒为急濑牵。会置轮机舒水力,更横高坝镇深渊。他时紫电传千里,神女应惊人胜天。”当时周总理看了笑道:“你双姓汪胡,又有工程师与诗人的双重人格。长江三峡的巨大能源是要开发的。”1983年,汪胡桢参加了三峡工程的可行性探讨,他激动不已,发出“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我还想背上行李去三峡工地大干一场”的坚强心声。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力不从心,于是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三峡工程出谋划策上面,先后发表了20多篇有关三峡大坝选型、船闸设计与移民工作等重大科研课题的论文,提出了不少大胆独创的设计构想。例如三峡坝型这一课题,他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亲自设计、计算,提出了“格箱式浇筑法代替柱状法”,设想创造混凝土格箱和土石格箱坝两种坝型。船闸是三峡工程中难度较大的一项工程,汪胡桢研究了古今中外的船闸,大胆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使江船一步升降137米水位差的井式船闸方案。我国自己能不能不靠外援而自行设计呢? 他老人家充满信心地说:“其实任何人设计水工建筑物都是从零开始的。我国几十年来的水利建设工程,除三门峡水库外,都是自己设计的。”他谆谆告诫大家:“不要忘记世界上首先发明船闸的是我国的先哲,这项发明领先于欧美各国两个世纪。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希望我国水利科学工作者能深入研究。
水库淹没区的居民迁移问题是建库工程中耗资巨大,且工作十分棘手的问题。过去是实行国家发给移民迁移费自行解决,此办法遗留问题多。后来用移民费建设移民区,虽然克服了不少移民生活居住困难的问题,但生产资料、发展生产等问题还没有解决。汪胡桢写出《怎样实施长江三峡水库经济开发性移民政策》的论文,他提出,应给移民营建经济林、建设水库渔业基地及兴办新工业区,使移民不但能在新地区居住生活,而且能从事生产,使移民费用变成企业投资,而后以生产税利形式再缴给国家。他的这种开发性的思想,在还没有市场经济观念的1983 年提出,是难能可贵的。当时得到了水利部领导的重视。如今,开发性移民政策已成为主要的移民政策。
汪胡桢很注重水利建设的经济效益。1981年,他写出了《水电工程的经济核算》、《自力更生开发水利资源》、《开发长江三峡水利必须改革经营体制》等论文,很早就意识到经济与市场的观念。他还建议长江水利从建设三峡水库起,就应采用企业体制作为经营方针,并对成立长江水利开发公司的组织、任务、效益作了具体的规划和分析。晚年的汪胡桢,不顾年老多病的身体,在水利科技上孜孜追求,锲而不舍;在学术上勇于开拓,不断探索进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汪胡桢一生著作甚多,根据国内有关图书馆编印的目录和汪胡桢亲属提供的资料统计,汪胡桢的著作(含编、译)达10本之多,公开发表的论文有41篇,未公开发表的有48篇,其他如回忆录、报告、发言等文章有45 篇。他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为水利事业已经作出那么多贡献的汪胡桢,仍自感不足。1989年9月,他得知有医术高明的苏联眼科专家来华的消息后,下决心要去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以求恢复视力重新笔耕。不料,20多天后的1989年10月13日,他竟与世长辞,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在追悼他的《光辉的榜样》一文中写道:“他毋需留下更多的遗言,他留下的是毕生的事业,他给我们的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光辉榜样。”
(贾本琪)
简 历
1897年7月12日 生于浙江省嘉兴市。
1917年 毕业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1922—1923年 在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
1923—1924年 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
1924—1926年 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
1927年 任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副总工程师。
1929年 任浙江省水利局副总工程师。
1930—1931年 任导淮委员会工务处设计组主任工程师、第十二区工赈局局长兼皖淮主任工程师。
1931—1949年 1931年起历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第二至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兼出版委员会主任。1936年任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
1934年 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
1935—1937年 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设计科长。
1938—1945年 先后在中国科学社、厚生出版社译书、编书。
1946年 任善后救济总署苏宁分署赈务组副组长,水利委员会派驻联合国救济总署上海办事处顾问。
1946—1948年 任浙江省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9年 任浙江大学教授,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1950—1954年 任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兼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工程部部长,佛子岭工程总指挥。
1954—1960年 任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总工程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
1955年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60—1978年 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名誉院长。
1978—1982年 任水利部顾问。
1989年10月13日 逝世于北京。
主 要 论 著
1 汪胡桢,周文德,李藕庄,等. 中国工程师手册.上海:厚生出版社,1944.
2 汪胡桢. 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7.
3 汪胡桢. 地下洞室的结构计算.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
4 汪胡桢. 罗汝梅,杨真荣,等.现代工程数学手册.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
5 汪胡桢. 重力坝的主应力网.北京:水利学报,1981(6):61-666.
6 汪胡桢. 长江三峡节水船闸的初步探讨.北京:水利学报,1983(7):47-537.
7 汪胡桢. 怎样实施长江三峡水库经济开发性移民政策.武汉:人民长江,1987(5):2-4.
参 考 文 献
[1]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代水工汪胡桢.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
[2]钱正英.光辉的榜样——向汪胡桢先生学习.中国水利,1989(12):3.
[3]李鹗鼎.怀念汪总.中国水利,1989(12):6.